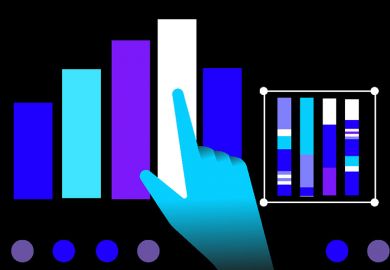点击阅读英文原文
几年前,当我在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研究和发展委员会任职时,我们经常受委托,决定一项提案到底是完整的研究,还是“仅仅”是一项审计。
后者涉及对辅助治疗的服务的评估,例如改变病人等候区或对护理体验进行反馈。这不能称为研究,因为它可能不会产生全新的、有效的知识。尽管事实上,审计要想变得有用,其准确基线、结果测量以及对易混淆的变量的认识(如果不是控制的话),应该像标准研究一样稳健。
研究和审计之间的区别很重要,因为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认为审计不需要遵循与研究相同的伦理审查。然而,这种干预可能会引发和研究一样多的道德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行政便利。鉴于医疗卫生领域进行的服务评估数量庞大,如果所有类似研究的活动都需要批准的话,伦理审查体系可能不堪重负。然而,行政便利显然不是决定伦理监督适用场所的好理由。
最近,我一直在经历挑战,以欧盟委员会一个名为PRO-RES的项目的领导者身份定义研究,该项目旨在促进非医学研究中的伦理和诚信——在其中某些领域,要求提交伦理审查有时会遭到激烈反对。
我的同事、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经济学家法比安·祖里格(Fabian Zuleeg)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研究机构都能够坚持PRO-RES项目关于研究中所寻求的价值观、原则和标准的基本声明。例如,声明可能会与一些智库的商业模式发生冲突,因为这些模式为不太可能遵循这些原则的信誉较低的组织提供了不正当的竞争优势。
但是,尽管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分析师可能不具备“研究人员”这一标签,他们当然也收集数据,并综合其他来源的研究结果。他们利用自己的判断和经验,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建议。那么,他们为何与学术研究者不同,目前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形式的伦理审查?
逃避伦理审查的不仅仅是公共政策研究人员和宣传组织。数据收集也是大多数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权宜之计——谷歌、亚马逊和脸书等公司实现巨额利润,证明了这些数据的价值、准确性和有效性。然而,目前没有适当的法律对它们的行为加以限制。它们可以只服从公司内部的规章制度。
研究中的标准适用于某些研究者,而不适用于其他研究者,怎么可以允许这种差别对待呢?这只会进一步迫使熟练的研究人员放弃大学里需要接受伦理审查的学术研究工作,转而投身薪酬更高的商业研究机构。在商业研究机构中,创新甚至可能凌驾于诚信之上,而且极不可能认同“开放、透明和知识共享”等所谓的科学基本原则。
选举唐纳德·特朗普并“造成”英国“脱欧”公投结果的研究,不受与学术研究人员同样的伦理和诚信审查。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是个“科研雇佣兵”——被用来收集足以对舆论产生大规模影响的数据,并且在利用数据时,不需要遵循透明、平衡和公正的原则。
数学家汉娜·弗莱(Hannah Fry)最近主张科学家——尤其是数学家——遵循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她希望通过这种做法,鼓励科学家更密切地关注以不同程度的许可收集和操纵个人数据的隐藏算法和无形的进程造成的严重后果,并采取对个人及其社区有现实影响的行动。
但我们也需要找到一些与传统的伦理研究监控模型相当的东西,这些模型可以应用于企业、智库、宣传机构、游说团体和更模糊的、以改变大众行为为目的的“咨询机构”。在个人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食品和农业科学等领域尤其应该如此。
这种情况尚未出现,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人考虑过如何做到这一点。但是,有关当局不应仅仅因为任务艰巨就止步不前。为“纯”学术研究建立监管机制可能更容易——但这类研究的危险性可能远远比不上目前尚未接受监管的研究。
如果说某些研究值得监控,那么所有研究都应该监控——以与其形式和功能相称的方式。允许非学术研究人员回避学术界无法回避的规则,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历史已经表明,依靠学术领域之外变幻莫测的自律来约束,是会导致规则滥用的。
罗恩·伊弗芬是一名独立研究顾问。这些观察结果来自他为斯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Springer Nature)编辑的《研究伦理和科学诚信手册》。该手册部分章节已在网上发布,完整版本将于2020年初发布。
后记
Print headline: Ethical review should not be for academic research on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