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阅读英文原文
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读研究生时,几乎阅读了我所研究的细菌趋化性领域的每一篇文章。我做到了,也因为完成了这项现在不可能完成的壮举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同事中闻名。
在我参加的一次关于微生物感官传导的戈登会议(Gordon conference)上,几位研究生、博士后研究者和一两位教授讨论了细菌在环境中化学物质浓度影响下产生的信号是如何传递的。尽管我当时资历很浅,但我并不害羞。在回应其他人的发言时,我插话说:“那这篇论文呢(我点名了作者)?”我得到的回答很惊人:“每个人都知道那篇论文是错误的。”
我惊呆了。在与更多资深研究者确认这是普遍观点并了解到原因之后,我询问这篇文章是否被撤回或改正,以及随后的论文是否指出这些数据是不正确的。答案是否定的。
让我们承认,我当时是一个天真的研究生。我问道:“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存在?”科学文献绝对应当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当前的知识。
当时人们会说,文献很少被更正,而且科学家常常不愿意指出他人出版物中的错误。但是问题仍然存在。那句“每个人都知道那篇论文是错误的”中的“每个人”是指谁?参加会议前的我并不知道,而我就处在这个领域中。那些不是这一领域、被误导或错误地引用这一错误文章的人呢?在已出版的和口碑相传的科学文章中,哪些是真正的主体,哪些是阴影?只有存在行为不当的文章需要撤稿,还是结果有误的文章也应撤稿?
让我再讲一讲更久以前的经历。当我在纽约市里弗戴尔的一所高中读书时,有一位深陷偏激人格的英语老师。他极度狂妄自大,对学生极尽贬低之能,并颇爱展示自己对特定追随者的无耻偏爱。我向高中校长投诉过他侮辱性和偏执的言辞,以及他显然在不阅读作业的情况下给作业评分的事实,但管理者在这两个方面都原谅了他的行为。
我最终得以转出他的班级,但后来我发现,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不过是大批逃离者的其中之一。而我的学校中还曾有多起针对教师性虐待的指控,受害人包括我的一些同学。我再次承认自己是一个天真的学生。当时我并不知道,也根本无法想象这些虐待。
但是我从这次事件中学到了两件事。首先,行政人员和机构经常在不当行为发生时未能采取行动,从而也不会为此承担责任。其次,有的人如果有一种令人不可接受的行为,通常也会在其他方面展现出此类行为。
我继续从经验中得到教训。作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的访问科学家,我参与了一个小组。该小组的工作成果最终成为了登上《自然》(Nature)杂志的两篇被频繁引用的文章。我试图复制自己在文献阅读上的壮举,想要阅读涉及一组现在被称为GTPases的重要分子的所有文章(这一名称因我和我的合著者而被广泛使用)。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我几乎就要完成了。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次尝试,因为随后有关该主题的文章数量激增。
在仔细阅读中,我发现该领域一位多产的作者似乎一遍又一遍地撰写基本相同的文章,只是蛋白质名称或蛋白质组织来源有所不同。在不同研究文章的方法部分之间允许文字重叠,但这些文章中的重叠贯穿始终。两篇高度相似的文章出现在两本不同的期刊上——几乎总是相同的这两本期刊;而出版日期之间只有很短的过渡时间。
有一次,我收到了一位多产作家的手稿,对其进行审阅。我认出了作者的写作风格,而一些数据已经在另一本期刊的一篇文章中出现过了。我和同事们把我们的担忧传达给该期刊的编辑,随后编辑联系了作者。但作者宣称自己无辜,是受害者。最终编辑在警告后放了他一马。
在我担任附属于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怀特海生物医学研究所(Whitehead Institute for Biomedical Research)的博士后研究员期间,曾发生过针对泰瑞莎·今西-加里(Thereza Imanishi-Kari)的不当行为的定期讨论。这一讨论关注她和戴维·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在1986年合著的论文;后者管理我所在实验室附近的实验室,并且是1975年诺贝尔奖的得主。接着,在罗伯特·温伯格实验室(Robert Weinberg)工作的麦克阿瑟(MacArthur,又称“天才补助金”,“genius grant”)研究员错误地声称发现了“癌症转移基因”,该实验室和我们在怀特海研究所的同一层。我的同僚科学家们的职业主义倾向,以及在某些方面仓促地抬举某些人而又不公正地阻碍其他人的、陈旧的熟人社交网络,在那里被清晰地展示出来。
我的博士后导师理查德·穆里根(Richard Mulligan)是利用病毒将遗传物质引入细胞进行基因治疗的先驱。我最初的项目是设计能针对特定细胞的经基因工程修饰过的逆转录病毒。但我最终意识到,我们对逆转录病毒进入细胞的正常过程了解得还不够,所以我集中精力填补这一不足。
可以进入细胞并传递遗传物质但不能复制的缺陷病毒是主要的实验工具。在我的研究中,多个实验室明显存在同一个问题。据称这些细胞实几乎无法产生可以繁殖的逆转录病毒,而实际上却在生成这种具有潜在危险性的病毒。我可以保证,这一发现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快,因此我们竭尽全力保密。
与逆转录病毒有关的材料是所有哺乳动物基因组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不同目的哺乳动物中的逆转病毒不一样。我们使用的缺陷病毒是在小鼠细胞中产生的小鼠病毒。它带来问题的潜在原因之一是,有缺陷的小鼠病毒与小鼠细胞中已经存在的物质结合在一起,可能导致逆转录病毒复制。一种解决方案是对人类细胞进行基因工程编辑,来生成有缺陷的小鼠病毒。在我们的众多协助下,另一个实验室中的一名研究员设计了这一实验并将其发表。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认识到这些细胞的实用性。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实验室收到了这些细胞。很快,我和一位同事发现细胞系的制备不正确,导入的核酸之一并不是文章中材料和方法部分所述的核酸,并且可传播的小鼠病毒物质已经被导入。我们通知了作者,并建议他们更正论文。
在冷泉港逆转录病毒会议上,一位研究生做了一个演讲,介绍了他的研究工作,他研究了如何利用人类细胞系传播另一种小鼠逆转录病毒(下称A病毒)。对于研究来说,这种机制似乎是完美的,因为在这种机制下没有其他任何可能干扰小鼠病毒的遗传物质,如来自B病毒的物质。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名学生报告说,他对细胞转移的遗传物质的分析发现了B病毒中的物质。
显而易见,这是前述论文作者导入细胞系的病毒材料。但是学生并不知情,他向听众寻求建议。在演讲结束后,我私下与他交流,并向他解释了这一发现的由来。他非常感谢我。他坚持认为,我避免了他在这一已经浪费了大量时间的项目上多做数年的无用功。
但可能其他人并不那么幸运。这篇未经修改的错误文章已被引用近3000次。
处于基因治疗领域有时并不利于保持对科学完整性的信心。穆里根实验室一直是娱乐的源泉;该实验室的另一篇“经典”文章中描绘的动脉壁的弥漫性染色被认为是基因转移的结果,但实际上不过是背景染色。除了1999年杰西·格辛格(Jesse Gelsinger)在早期基因疗法实验中广为人知的不幸去世外,还有其他被忽视的、草率的人类研究和动物数据。
在我对负责修饰的逆转录病毒进入细胞的蛋白质的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些错误的发表数据。我与一些作者联系,几乎说明了错误是如何产生的,但这却永远无法让他们承认问题所在,更别提纠正自己的文章了。
在一个例子中,我联系了一位实验室负责人,我与此人有私交。他发表了一篇肯定是错误的文章,其结论对我自己的研究有直接影响。我分享了我的分析结果,并请他将自称已产出的材料发给我,以便我直接对其进行测试。
他先是告诉我,这些材料在最近一次搬家中丢失了,他会让实验室里的人重新制作。过了一阵,他说重新制作材料时产生了错误。最后,他什么也没给我。可能值得一提的是,该科学家后来因对14岁以下儿童进行性虐待而被定罪(请参阅我从高中经验中学到的教训)。
在另一个令人不安的例子中,我们实验室与合作者一起向主要科学杂志(A期刊)提交了一份关于我们对一种酶的结构的研究稿件。过了一阵,我们收到了拒稿通知。奇怪的是,同一天,一篇关于与这种酶紧密相关的蛋白结构的文章以“加速”出版的形式在B期刊发表了(这意味着在其提交和发表之间的时间比一般要短)。当时我注意到了这一巧合,但只是对此感到困惑。
在根据审议者的评论进行修改后,我们的文章被另一本受人尊敬的期刊(C期刊)接受。随后,曾加速发表论文的小组又在D期刊发表了另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引用了一个假设,并把我们在C期刊的论文列为参考文献。该假设出现在我们投稿于A期刊的稿件,而非C期刊的稿件中,因此并没有出现在已发表的文章中。
一个合理的推论是,该小组接触到了我们提交给A期刊的手稿,加紧把自己的文章投给了B期刊,并且依靠他们对我们手稿的记忆,而非阅读我们在C期刊中发表的文章,写出了刊载在D期刊的文章。这意味着他们违反了同行审议的保密性,这是一种研究失当行为。
我联系了D期刊的编辑,他同意这件事有可疑之处。当我们联系A期刊的编辑时,他进行了非常粗略的调查,并根据作者的陈述说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解释说,他们找到了一个会议摘要,里面提及了我们删去的假设,并以此为依据来为自己重复引用从未提及该假设的文章进行辩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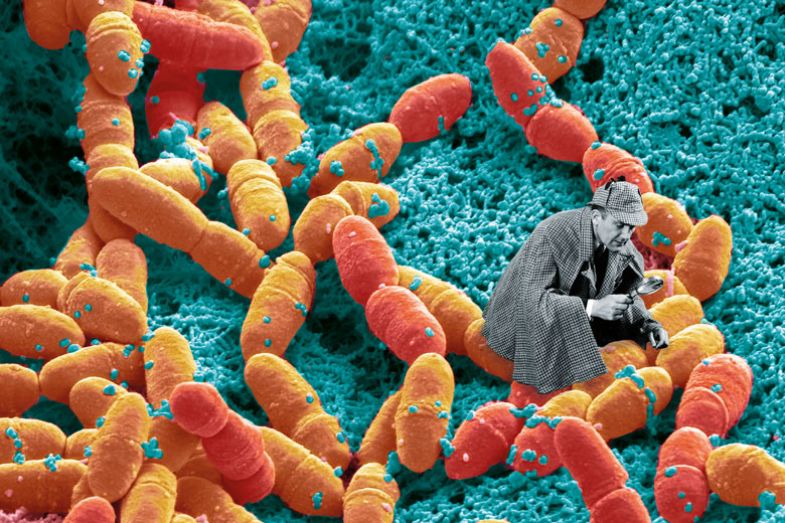
但直到几年后,我进行学术调查的分水岭才到来。
2010年下半年,在前往自己在普渡大学的办公室途中,我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听到了一条关于一种细菌的报道。据称该细菌使用砷盐酸代替磷盐酸作为营养物,并且砷在其细胞DNA中代替了一些磷。我以研究生和教职人员的身份研究过酶促磷酸基转移,并且知道报道所称的结果是不可能的。生物学可以教会我们有关新型化学的知识,但是生物学并不违反化学定律。
我对论文中数据的分析,尤其是对补充材料的分析表明,作者应当了解其主张的无效性,以及他们的结果是因为化学污染。尽管如此,这篇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仍受到国际媒体的报道。这一研究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该机构为这项研究提供了部分资金)一场新闻发布会的主题。NASA的邀请函上写道,这是一项“将影响寻找外星生命证据的天体生物学发现”。
其他科学家也迅速发现并公开了这篇文章中的许多缺陷。《科学》杂志发表了8篇针对此文章的重要技术评论和2篇反对其结论的驳斥文章。然而,该文章从未被撤销,仍在被引用,有时就好像其中有一些有价值的内容一样。NASA、吹捧这项研究或对其错误一笔带过的报道者也没有公开承认过他们的错误。
我尽了最大努力,但于事无补。我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在博客上发表了评论,并与作者、《科学》的主编和记者在线上沟通。由于我在这一事件中的显眼表现,我被邀请到在世界各地举办的、有关该议题的研讨会。此事件是扭曲科学事业力量的典型;而我说明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
这些讲座不断激起与我传达的观点有关的最广泛的讨论。最有趣的是人们在此后大多频繁地与我联系并分享自己经历。他们说:“如果你认为这很糟糕,那应该看看这个!”他们会要求我提供建议或调查其他违反科学规范的行为。我还收到过电子情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研究计划的开始。
我不是第一个聚焦研究不当行为的调查者,也不是最多产的。我的许多同僚都比我更有能力。而一个积极的进展是,过去几年中进行调查的人数有所增加。有些人实际上发现了一些无赖的整个关系网。尽管如此,很少有人在对科学文献进行初步查询的时候,愿意使用自己的名字。此外,没有多少人能像我一样同时发现数据造假和抄袭。
每次获得一些情报后,我都会审阅所涉及的文章,并决定是否应跟进。如果文章严重偏离科学标准,我将继续审查该作者的其他文章。我的经验是,在一份出版物中表现出不正直的人,这种行为也会出现在该作者的其他发表中。我相信其他进行调查的同僚也有同感。同样,虽然很多人重复进行同样的违规行为,他们也会犯下数个错误。
一般来说,我并不认识这些作者。因此如果有重大问题,我会通知相关期刊。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遇到过极不愿意采取行动的编辑。哪怕数据或文章明显存在问题,作者很少愿意承认,而编辑似乎乐意接受作者的说辞。我和一位合著者曾列出过作者提供并被编辑接受的不合逻辑的借口。在一些情况下,只有媒体人士表示兴趣后,相关人员才会采取行动。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期刊认识到作者的诚信和信誉确实存在问题,因此改变了政策以解决这些问题。我曾亲自向一些期刊介绍我的分析结果,这些结果使十多篇论文得到更正或撤回。坚持就是胜利。
然而,大部分期刊都遵循着忽视和拖延补救措施的传统。而且,对科学文献的修改实际上是对我花费在调查中的许多小时的唯一回报。这对我的职业发展毫无益处。此外,一些学者对我的行为表示不满,并采取行动破坏我的调查,包括起诉至法院。
如果我匿名举报这些研究不当行为,能更容易避免那些来自亵渎行为标准的人及其同伙的报复。我当然理解为什么有些举报人想隐瞒自己的身份。但是,致力于公开批评科学文献错误的人失败得越多,犯错的人被成功锁定的可能性就越小。此外,匿名与现代科学事业的准则相悖。
我认识的大多数科学家在进行研究和报告研究时都十分诚实。科学仍然是解决社会所面临挑战的最佳基石。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科学遭到反对者的攻击。一些同事担心,揭露研究人员的不当行为会强化科学的敌人。但是,那些不遵守科学规范的人才是破坏公众信任的人。他们占用了资源,正直的研究者就得不到资源。他们也为年轻科学家树立了坏榜样。
研究界不应奖励作弊者——这会增加公众的不信任感。大家也不应该对不当行为视而不见。也许我仍然很天真,但在我看来,即使在后真理社会中,每位科学家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站出来捍卫真理。
科学必须自我纠察。为此提供帮助的人应该受到赞扬而非谴责。
大卫·桑德斯(David Sanders)系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生物学系的一名副教授。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