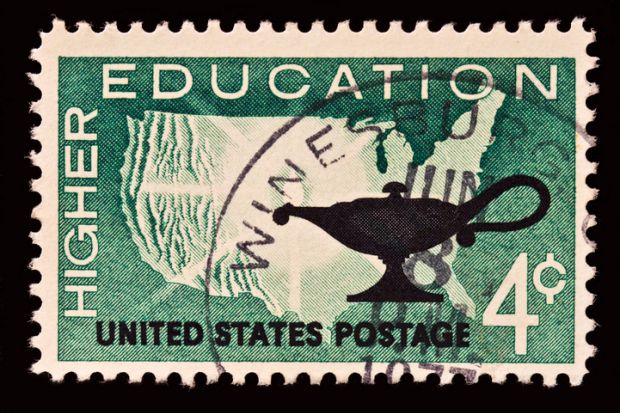点击阅读英文原文
关于20世纪60年代对高校、学习和学术的影响,学术和流行写作都发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变化。它们从纯粹的赞美(通常带有对消逝的黄金年代的赞歌)变为无情的谴责,同时在这两种极端中也有许多其他声音。
在政治上的右翼看来,20世纪60年代往往被视为学术(至少在某些学科)从追求真理转向追求社会变革的时期。绝非偶然的是,保守派学者也立即指责那些与它们意见相左的人是“政治化的”因而是有偏见的,但却对跨越学术诚信界限的保守派同行——从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Wowell)和历史学家彼得·伍德(Peter Wood),到政治理论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语言学家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都只字不提。
许多左翼人士战略性地接受了这种轻视,他们试图争辩说,他们的研究远没有被“政治化”,实际上是对真理的存粹客观的、无私的追求。双方都没有把握住上世纪60年代许多著名学者的观点:学术不可避免的具有政治性,但不必因此而带有党派色彩或狭隘的意识形态色彩。
但我们不应坚持这种具有误导性的二元对立,而需要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概念化。学术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运用的一套综合的解释行为;这些语境包括时间、空间和当下的对话与辩论。这些社会化、知识性的过程同时兼顾社会和知识这两个维度,不仅包含学科“既往智慧”的“传统”或“叙事”,还包含新的问题、来源、方法、比较和解释性重点。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所有的知识都是其自身环境、实践和地点的产物。没有一种是普遍的、永恒的,也没有一种是无法被挑战的——就像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62年在科学领域所展示的那样。客观性和主观性存在于一个范围内,它们不是两极对立的。
在遵循基于事实的研究、透明的分析、明确的假设陈述以及对有争议的观点负责任的批判性比较等专业标准方面,有很多例子。例如,我想到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革命时代:欧洲,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Europe, 1789-1848, 1962)和《劳动者:劳工史研究》(Labouring Me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1964)。在大西洋另一侧,我想起了迈克尔·B·卡茨(Michael B. Katz)的《改善穷人:福利国家、“下层阶级”和城市学校的历史》(Improving Poor People: The Welfare State, the “Underclass,” and Urban Schools as History, 1995)和《不配的穷人:美国与贫困的持久对抗》(The Undeserving Poor: America’s Enduring Confrontation with Poverty, 2013年第二版)。
在地理学方面,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差别的公平、自然和地理》(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1996)和《反抗的城市:从城市的权利到都市革命》(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2012)就是很好的例子。在政治学方面,有艾拉·卡兹纳尔逊(Ira Katznelson)的《马克思主义与城市》(Marxism and the City, 1992)或《恐惧本身:新政与我们时代的起源》(Fear Itself: The New Deal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2013)。
此外,还有社会学领域的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和英语研究领域的约翰·吉洛里(John Guillory)的相关著作,以及其他横跨不同学科和解释立场的著作。作为个人和群体,他们都展现出了理智的自我约束,以及执着的学术研究的力量。
这也是我也曾试图走过的一条道路。上世纪60年代末在研究生院的时候,我的教授告诉我,如果我研究相关的文献,如果我的问题有恰当的语境和解释,如果我的研究(包括资料和方法)是彻底的和透明的,如果我的论点和结论可以接受同行的审查,我就可以合理地提出新的解释,并支持这一解释代表的立场。
我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这种方法:从我的第一本书开始,从量化和质化两方面探讨了识字率的历史水平以及识字率分布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意义。我的问题让我把当时仍属新颖的社会史、城市史、人口史和量化史与传统的方法和资料结合起来。其结果是对我所定义的“扫盲神话”(同名书籍The Literacy Myth 出版于1979年)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挑战;“扫盲神话”这一没有确切记载的看法认为扫盲本身具有独立的变革性影响,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另一本书《冲突之路:成长于美国》(Conflicting Paths: Growing Up in America, 1995)通过一位“新社会”历史学家的视角,对500多篇关于童年、青春期和青年的第一人称叙述进行了社会文化分析或小说“解读”。我确立了不同的主要成长模式,以及它们随时间产生的变化。
这些研究项目被公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并为历史的重新解释、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以及社会和制度政策提供建议。这些都是学术的合理延伸。
认为修正主义是可耻的,应该被谴责为“政治化”或“现世主义”的想法,相当于一种误导,让人回想起一个充满经典和客观真理的神话般的黄金时代。认识论的误解太容易与意识形态相结合,从而将事实与发现分开,而不是将它们联系起来并进行质疑。
在以事实为基础的、知识渊博的、负责任的和诚实论证的学术中,客观性和倡导性不一定是对立的,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关键教训之一。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并付出了无比的代价。
哈维·J·格拉夫是俄亥俄州立大学(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的英语和历史系荣誉教授,也是首位俄亥俄州识字研究的杰出学者。他著有许多关于社会史、读写和教育史,以及跨学科研究的书籍。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后记
Print headline: The best scholarship is political but not partisan or ideologi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