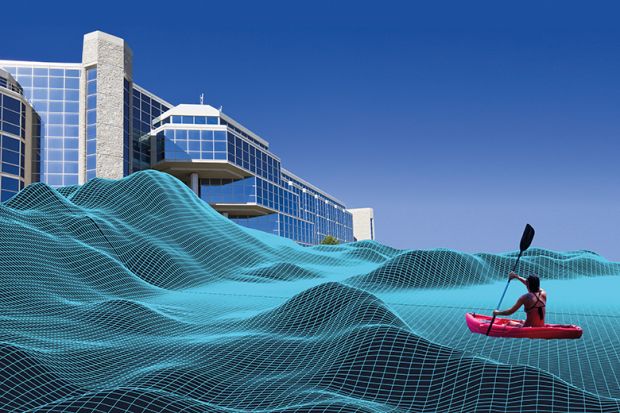点击阅读英文原文
“当这一切结束后,我会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带着孩子去工作”
问问学者们对于校园工作的所念所怨,你可能会对他们的答案感到惊讶。我指的是真正的答案,而不是公关认可的标准答案。当然,学者们非常想念所有优秀的付费学生、他们的同事、出色的校园建筑和设施,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学生。谢谢你,来自媒体办公室的西蒙如是说。
但学者们不愿公开的真实想法呢?想念学生?当然。至少是那些可爱的学生。同事呢?这就复杂了。当然会想念其中的几个:至少是那些我们选择与之合作的人。但大多数部门与只在这一点上与家庭相似:都是命运随机地将一群奇特的人抛在一起、迫使他们共存,而且屡试不爽。
教职员真正怀念校园生活的哪些方面?看看在办公桌上随机堆满的文件和从2008年开始就没打开的信件吧。没有什么比这些巨量的废纸堆更能在学者的世界里创造一种秩序感了,而且它们还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藏身地。或者,看看他们最喜欢的盆栽植物。事实证明,这种植物对缺乏照看的生活很适应,所以确实也应该划入初级教职员之列。又或者是看看他们隐藏的酒柜,保存完好,远离人事部门的窥探。
教职员不怀念校园生活的哪些方面?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一个总是尽可能在家工作的人,所以这个居家办公“新世界”的一些方面对我很有吸引力。它更有效率,也与养育孩子的责任更兼容。我不需要去赶那些后来晚点的火车,也避免了与公共打印机、咖啡机、任何公共物品纠缠(你最近有没有闻一下你们部门公共冰箱的味道?)。这意味着你不必忍受一间像廉价汽车旅馆床一样乱颤,在三叠纪时期就开始建造的办公室。
额外的好处是,你再也不用在冗长乏味的委员会会议上假装专心听讲了。现在你可以关掉你的视频和麦克风,泡一杯茶,希望没有人问你问题。也就是说,在疫情封锁时开会,会议往往简短、高效、充满幽默。坐在我两边的四五岁的孩子们就像一对缩小版劫持人质者(像不耐烦的定时炸弹滴答作响),如果他想尝试和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一些不相干的事情,那么祝他好运。当这一切结束后,我会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带着孩子去工作。
撇开一切浮躁不谈,还值得记住的是(就像几天前有人在推文中说的那样):不管感受如何,我们不是“在家工作”;我们是“在危机期间,待在家里、努力工作”, 最重要的是,我们尽其所能,努力拯救生命。大多数曾经重要的事情现在都不重要了。
所以,我想对我的同行说:保持安全,待在家里。如果你有孩子,就把他们“当作武器”对抗生活;如果没有,就尽情享受杜松子酒和盒装酒的美味吧。当我们都回到办公室时,也许可以削减一些职业生涯中的冗余之物,这样,下次一些锐意改革人士试图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时,“我不怀念的事情”的清单就会短得多。
克里斯·钱伯斯(Chris Chambers)系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心理学院的教授和脑刺激学科的负责人。

“教授是可以被取代的,但一个好秘书可是一个部门的大脑中枢”
每天早上,当我气喘吁吁地爬上两层旧大楼的楼梯,走进我们部门时,首先进入主办公室。我查一下邮箱,把垃圾邮件丢掉回收,和秘书们聊聊天。
德国大学通常会为每位教授安排一名兼职秘书,作为繁重行政事务的一项补偿。多年前,我的同事们就决定将他们的秘书人员集中起来,在一个常常把教员互相隔离开的体系中,安置一个中心枢纽。我曾经以为自己只是去主办公室拿邮件的,但现在我意识到,这种每天的例行公事实际上是一种与他人沟通的方式,然后我就会孤独地看着空白网页或忍受电子邮件的匿名噪音。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非常怀念它,因为部门已经关闭了,我所有的工作交流都安排完毕,只在电脑上交接,专注于完成各种任务。
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对秘书怀有深深的敬意,虽然我确实有。在学生时代,我也曾做过秘书(当时的名头更花哨一点——“行政助理”)。很快我就认识到,我可以通过别人对待我的职位的方式来判断其性格。我在第一份教职工作中曾服务于某位主席,他让来学校的求职者在主办公室里等了半个小时。工作人员关于他们在认为自己没有被面试时的行为报告很能说明问题。教授是可以被取代的,但一个好秘书可是一个部门的大脑中枢,他们能预见潜在的问题,知道在更高的级别上谁能够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正如我所说的,这并不是我怀念与秘书人员日常交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在一个往往对个体冷漠无情的系统中,他们一直源源不断地带来善良、温暖和明智的建议。
这些女性曾与我一起嘲笑大学生活中的荒谬事;当我与大学管理部门交涉无果心情沮丧但努力不哭时,她们表示了同情。当看到我带着重病来上班,她们毫不含糊地让我回家休息;当幼儿园的罢工或学校的假期迫使我带儿子去上班时,她们会拿出彩色铅笔和大量糖果。
我很想见到他们,因为我们的谈话充满了实用主义和人性关怀。他们提醒我,一个机构不仅仅是它的虚名荣耀和自命不凡:它是一张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之网,由微小的习惯和日常关怀的姿态编织而成。
伊莉娜·杜米迪斯古(Irina Dumitrescu)系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英国中世纪研究的教授。

“大型电话会议最好的一点是,它给了你整理办公室的好机会”
我是一个自我隔离的“老手”,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家工作。
我研究生命科学,具体来说是农作物疾病,但具体的实验室工作是由我的学生和博士后完成的。我不能说我怀念在实验台上的工作,我想,如果我穿上实验服,追问着“这些天我们把吸量管放在哪儿了”此类的问题,他们一定会生气反抗我的。但我确实怀念去温室和生长间,跟踪和评估症状的发展。我也怀念在茶室或图书馆翻阅纸质期刊的日子。在澳大利亚工作过后,能去一些比较冷的地方很不错;在丹麦工作过之后,能去一个温暖的地方工作也很好了。
大量正式的小组指导,甚至社交互动都可以被线上对话所取代,但这是有限制的。在家工作并不能取代周五下午为庆祝博士论文答辩、获得资助或论文发表的聚会。虽然在网上进行愉快的对话很容易,但是,当聚合酶链反应系统工作而结果不确定,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实验失败,这时要进行深度的对话就难多了。我不知道如何在家里舒适的办公室里开始组建新小组成员,虽然严格执行工作日程也能维持生产效率,但我发现只要我们被禁止返校,就很难互检奇怪或者异常的结果。
在家工作可以是非常高效的。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独立实验室加办公室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了,但是你可以建造独立办公的家庭办公室,这样一切都如你所愿。我当然不想再经历50米的长途跋涉跑到打印机前却发现,要么就是我没有按“打印”键,要么就是纸用完了。几年前,有几个月的时间我每周有一天待在家里,这让我得以完成自己的第一本书。
但我确实想念参加会议的时光。最后一次是在罗马,当时伦巴第刚刚报道了首例新冠病毒死亡案例。从那以后,我原本要参加的所有活动都被推迟或取消了。在我的日程安排中,下一个确定的出行事件是在2023年。
这促使人们尝试各种形式的大规模在线活动,而我正在努力配合他们表现得很热情。大型电话会议最好的一点是,它给了你整理办公室和电脑桌面的好机会。
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可能被认为肮脏的秘密。我们喜欢参加会议,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新的信息,或者是为了与同伴交流。会议的主要诱惑在于,这是你所在学科领域的戏剧性(包括智力和人性方面)得以展现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以观察者的角度观看一切。
理查德·奥利弗(Richard Oliver)最近从西澳大利亚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 Western Australia)农业科学杰出教授(John Curti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的职位上退休。

“每次只工作一两个小时还谈效率,似乎有点可笑”
起初我最怀念的校园生活是日常规律的安全感。但是,在家工作几周后,我们现在忙碌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不止有了自身的节奏,更凸显了与疫情大流行前的生活方式的不同——这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
尽管在照顾两个学步期的孩子这一方面要作出很大调整(工作也是),但我一点儿也不怀念早上急急忙忙每个人准备好、送孩子上日托大哭大闹的生活。新一天的开始变得愉快多了——虽然让孩子们穿上衣服的难度大致相同。
诚然,我确实怀念办公室里宁静的环境和非常私人的空间,这是我成为教授时最渴望的特权之一。但我正在寻找方法,在没有这些的情况下,实现迫切需求的平衡。
虽然每次只工作一两个小时还谈效率,似乎有点可笑,但我并不怀念自己迫于工作效率而像奴隶一样对着办公桌和电脑工作。很明显,算一算我坐在办公室椅子上的时间,我的工作效率并不是特别高。而且我一点儿也不怀念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因为“太忙”而无法联系、好好谈一谈的日子。
出人意料的交流已经出现了,我非常希望在隔离结束后仍然保持联系,就像每周一次的视频文献报告会,汇集了行业内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主要调查人员和学员。第一次会议有65名与会者,他们之间进行了非常活跃的讨论;平时大家最多只能在一年一度的会议上进行互动。就像生物学家研究有机体对环境压力的反应一样,我很想知道一旦去除居家隔离这个“实验条件”,那么这些在教学和科学交流中的调整是否会成为永久性的、积极的创新举动。
我原本认为自己会想念和学生们在课堂上的互动。是也不是,因为我发现,比方说,用在线论坛取代讲座,实际上比我的现场讲座反映出更多问题。虽然我对现场讲课同等重视,但我也开始发现线上和不同步的方式可以支持更多类型的学习者(及其个性)。
我发现我最怀念的人与人之间实际互动的小细节。尤其是看到一群人从我敞开的办公室门前走过:我的博士后步伐坚定,前臂上挎着她的“厨房水槽”手袋;我的研究生带着一个问题来到我门前时,她满脸歉意地低下头;另一个学生高兴地挥手说早上好。
“要是没有人也能搞科学就好了,”我以前常常开玩笑说——这是我在研究小组里管理人性时的一种揶揄。但现在,我渴望已久的那扇门终于关上了,我不知道何时才能有幸重开。
杰西卡·泽利格(Jessica Seeliger)系纽约石溪大学(Stony Brook University, New York)药理学副教授。

“在佛蒙特州乡下的阁楼里教学,这让一些学生疑惑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上课”
我在3月10日上了最后一堂实体课。为了避免乘坐纽约地铁,那天我骑了65个街区的单车去上班。这似乎是个好主意,但我不是唯一一个骑着共享单车上下班的纽约人。当我到达的时候,在学校附近连个停靠点都找不到。
我最终还是把自行车停靠好,但却是在另一个社区,而我跑了6个街区才回到教室。最终,我的最后一节课迟到了10分钟,上气不接下气,心慌意乱。这完全是一场灾难。幸运的是,听课的人也很少。甚至在闭校之前,学生就已经陆续返回世界各地的家中了。
自3月底以来,我一直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教书:佛蒙特州北部的一座旧农舍。离开我们在曼哈顿的小高层公寓并不容易。但由于家中有2位教授要在网上授课,2位青少年要在网上学习,对我的家人来说,暂时搬到一个更大的房子是必要的,并非奢侈。回想我们在纽约的最后几天,来到这里也是一种解脱。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地方让人怀念。纽约昂贵、肮脏、嘈杂,但它总是很有趣。这正是我的大学吸引学生的地方。他们来这里建乐队、成名、与艺术界人士建立联系,并在博物馆、出版社和媒体公司获得实习机会。我喜欢认为我的课程很重要,但是环境和课程同样重要。由于这个原因,在离加拿大边境不远的一个百岁高龄的乡村老阁楼上进行在线教学,不仅仅颠覆了我的授课模式。这也让我的一些学生疑惑,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样上课。
我欣赏他们的观点,但我也不断提醒他们,文化并不局限于城市。作为证据,我甚至开始分享我在农村新生活的照片。上周,我在一个旧谷仓里发现了一张被遗忘的旧日生活照片。照片的口号——“开始我们光荣而默默无闻的使命”——似乎出奇地合乎时机。但这并不是我分享这张照片的唯一原因。
作为一名文化研究学者,日常生活理论是我课程的一部分。通常,说服学生相信日常生活可能也很有趣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此时,这一点儿不费劲。没有什么比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可见、有价值带来的陌生感更震撼人心了。这可能是当前的混乱给我和我的学生共同上的一课:一个不请自来的机会,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壮观的景象转移到日常生活中。
凯特·艾什霍恩(Kate Eichhorn)系纽约新学院大学(The New School in New York City)的文化与媒体研究副教授和主任。

“我担心我的教学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
我的历史博士学位是在托马斯·杰斐逊建立的“学术村”里完成的。这个村庄的传统之一——该村庄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是让学生称呼老师为“先生”或“女士”;正如杰斐逊所希望的那样,而“Dr.”这个头衔是专门为医生保留的。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感受到这个传统的公正。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创造了一种新局面,在必需职业和非必需职业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线。毫不奇怪,不同的国家对此有不同的分类标准。在法国,面包房和药房被指定为“首要必需品”。在号称“孤星共和国”的德克萨斯州,两家长期以来相互依赖的企业——枪支商店和急诊室——门外都排着长队。
和其他地方一样,德州的大学也仍然对商业开放;与其它地方一样,除了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的利伯蒂大学(Liberty University)这两个例外,大学已完全转至线上。但当我艰难地上网课时,我担心我的教学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虽然我想念校园里的许多事情,但我最想念的是有意义的、必要的活动。把老师带出教室,这个职业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
毫无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的错。我与电脑的关系并不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中猿类与巨石的关系好多少。我在浏览交互平台的时候边咕哝边挠脑袋。当成功地与学生连接时,我却无法在更深的意义上与他们建立联系。我承认,Zoom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但我担心,它也代表了对有效教学的一种阻碍。
这里我应该引用柏拉图关于从口语到书面语的转变,或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关于媒介即信息的理论,但是我就不烦你们了。奇怪的是:当我盯着屏幕上那一摞摞学生面孔的方框时,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在主持一场研讨会。相反,我感觉自己被迫玩着塔罗牌的游戏。他们预示的未来中,我可能永远都无法再成为不可或缺的专业人才。
罗伯特·扎雷茨基(Robert Zaretsky)系休斯敦大学(University of Houston)菁英学院的教授。

“我甚至怀念图书馆里那些咯咯的笑声、吃零食的咔咔声和校园情侣爱抚的摩挲声”
现在他们都走了,我已经看到了日常工作生活的全部意义:与同事在我们城市大学的草地上,沐浴阳光共进午餐;通勤时间与半小时播客的长度完美契合;还有“下班后”那一刻的美妙感觉,那时我会关上电脑,尽情享受夜晚的无尽美妙。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想念图书馆。我怀念那些书的味道,保存多年只在我拿起时才得见光明。我想念它沉闷、勤勉的学习环境,是的,我甚至想念它不那么安静的咯咯笑声、吃零食的咔咔声和校园情侣爱抚的摩挲声。
图书馆是高校社区共享事业的实际体现。不仅仅是一个社区构成的集体,这其中既离不开四面八方的学生、查阅资料的学者、无数图书的作者、图书分类和数字化存储的图书馆员,也离不开门口的保安、咖啡师、搬运书本的人。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我有几次这样想过吗?而我现在的回忆给它加上了怎样的滤镜?
一段时间以来,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一直依赖于不断增长的学生债务、不稳定的岗位以及对海外学生和市场投资的经济效益。这不是一个值得留恋的体系,当这场疫情大流行结束时,我希望这个体系能摆脱对临时合同和有限资源投资的依赖。
然而,高等教育绝不是唯一一个越来越依赖这种做法的部门,在大流行期间被解约职工的困境暴露了这一点。事实上,整个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契约——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契约——将被这场危机重塑,大学也将随之被重塑。
因此,当我回顾那些曾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时,我也在展望未来,并努力思考在未来的岁月里,高等教育机构如何能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可持续的社会作出贡献。
塔姆森·皮特什(Tamson Pietsch)系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社会与政治科学的副教授。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后记
Print headline: Life in the Zoomiverse: what we miss about camp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