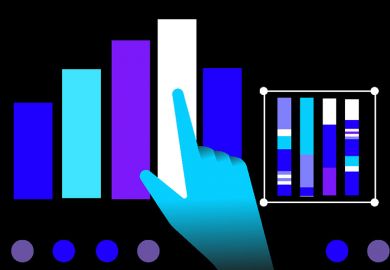一位教授在研讨会开始时这样指导:如果学生想要成功,他们必须学会像她一样思考。她分发了一本加了批注的十四行诗,要求学生按照她的方式给十四行诗加批,并且整个课程都要上交作业来获得学分。在第二周,她注意到学生们参加研讨会的穿着太随意了——毕竟她可没有穿牛仔裤。如果学生确实想在课程上获得好成绩,那就不得不穿得更专业些,像她一样。整个学期,她时不时分发在邮件中收到的衣服目录表,并圈出物品让他们购买。
学生们尽职尽责地交上加批的十四行诗,还有些人刷光信用卡买新衣服。然而,按照要求读十四行诗、模仿教授的穿着最终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她对论文的评论无益而刻薄:当学生尝试使用学术用词时,批评他们“傲慢”;当学生通过荣格原型进行解释时,嘲笑他们“愚蠢”。学生们已经努力了却无法从她那里获得确切的成绩。她只会说,他们获得了"有条件通过",接着又补充说,成绩的撤回不受时间限制。到学期结束时,学生们并不在乎自己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他们从未拿回期末论文——只想再也不要跟她打交道。
我曾试着将她的怪诞行径合理化:也许她是好心办坏事。也许她认为自己只是在坚持抵抗标准的下降,或者是将大学的使命付诸实践。但是,想想她的折磨所造成的伤害,这一切似乎都没有说服力。不管她的意图是什么,她的做法都透露出一种命令、欺凌和欺负的欲望:把学生纳入她的统治之下。正如她的一个学生描述的那样,简而言之,她就是一个控制狂。
学术界充满了痴人和怪人——"聪慧成痴"正是其吸引人的地方。在这里,强烈的动力和激光般的专注力可以带来诸多益处:吸引学生研究学问、创造新的知识、提升个人和机构的声誉。这是一个充满极端因素的世界。有神经兮兮的教授忙着微调他的实验设备,甚至完全忽略了外部世界。但也有另一种极端的教授:把他的学生和同事当作所有物受他操纵,事无巨细都归他管理。现在,神经兮兮型的教授比我刚入行时变少了点。但据我每年在高等教育工作所见,操纵型似乎在成倍增加。
这种控制狂就像学术界的龙卷风:浮夸妄大,所到之处,摧毁一切。他们是冷酷无情的评分师、难以相处的同事、苛刻逼人的管理员。他们享受构建复杂的迷局,用以表扬做得好的人,迫使顽固分子就范,而不服从他的人将要受到惩罚。
例如,推特上有份来自教学大纲的电子使用须知,揭示了控制狂的不良行为。它的开篇说道:"我礼貌地要求你不要在课堂上给任何人发电子邮件、发短信、拍照、打电话、用快拍、发消息(等等)。”学生要想在课堂上使用电脑,必须写一封“正式的、签名的申请,我(教授)将存档”。按照规定,学生承诺上课时关闭无线网,并且他们"在上课时,永远不上网,不发电子邮件、发消息、拍照、刷脸书或者浏览任何其他网站"。"不遵守合约"将会被扣分,并视为"不尊重"教授的意愿。
这种规定让我们了解控制狂如何构建其世界。教学大纲居然是一项法令。这种须知竟是一份合约。不是知识而是道德的失败塑造了整个课程。每一个“永不”的响起,都伴随着教鞭的啪啪作响。教授真的是在礼貌地询问吗?如果在课堂上使用电脑都被视为一种不尊重,那么教授的询问就算不上有礼貌。
作为一名学生,开学第一天你就拿到了这个。这能引导学习吗?恰恰相反,在教学大纲试图构建的教室里,学生被要求通过作家、社会活动家奥瑞德·洛德(Audre Lorde)所说的"几近于消失的消极被动"来取得成功。学习的实践必然会成为一团乱麻,因此不需要实践。事实上,没有什么可学的,因为学习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权力。

高等教育控制狂的折磨行径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后果。在大学的日常生活里随处可见它对人们紧张性抽搐的影响。一位求职者曾经在面试结束时严肃地问我,我是否注意到他鞋带的蝴蝶结是不对称的:他的完美主义顾问在模拟面试中指出这是一个致命的过失。有一次,一位同事在会议中耽误了15分钟,只因为她从文件里取下订书钉后,控制狂前主席要求她必须严格按照自己指出的角度重新钉上。
我问自己,这些控制狂从何而来。高等教育这个情绪高压锅提供了一种答案:超额完成任务是衡量我们的标准。我们建议研究生写的论文,不仅现在能通过审阅,而且还能在未来成为“热议”话题,仿佛我们能控制未来的国际学科走势。工作面试提供了一个迷惑和恐吓的机会。对于那些在有望获得终身教职的人来说,高等教育对评估的执着极大增强了他们的控制欲:你不能只是足够好,你必须是优秀的,不只是一方面,而是方方面面都很出色。(我曾经亲眼目睹一群终身教师起草了一份"优质"出版物清单,据此确定初级教师的绩效工资,而他们自身却尚未在这些出版物上发表过研究。)这么多人不断制定新的标准,然后凌驾于我们面前,难怪我们会试图把教室(这个我们尚有主权的空间)——变成自己的私人王国。然而,这样做并没有缓解学术界的结构性毒性。这只是一种最肤浅、最恶毒的模仿罢了。
控制狂过着不能跳舞的编舞生活,谱写不成诗歌的韵律。他们的世界中理想变成了呼呼抽打的教鞭。我们需要抵制一个教授不能唱歌、不能笑、不能表现出脆弱或快乐的世界。这个世界威胁要吞灭我们。即使是行政人员也不能幸免。一名临时校长被拍到在当地一家酒吧喝酒,然后对他"道德败坏"的指控广为流传,未及真相大白他就辞职了。“大学校长是个7乘24小时的全天候职业,是大学的脸面。”教务处副处长在一份官方声明中这样宣称。控制狂会抓住所有机会闯入我们的生活:没有职业和个人、公共和私人的界限。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会在我们的睡梦中继续缠着我们——也许有时候他们确实做到了。
那么,我们如何保护彼此免受控制狂的折磨呢?如果我们跳出他们严酷的套路,会大有帮助。作为一名教职员工,你可以确保自己做出那些控制狂所憎恶的事情:大笑、做双关语、放松。当这些现实主义者又和你谈起那怪异的不满清单时,一笑置之吧。如果他们用细枝末节压倒你,和他们谈谈大局观念。如果他们说天空要塌了时,你自己到外面去看一看。
我们也可以通过做理性的大学公民来下调情绪温度。不要将服务的角色外包给控制狂。如果他们必须参加评估,确保他们在委员会工作。记住,控制狂喜欢用诸如"优异"、"质量"、"卓越"和"优秀"等词语来展示他们拥有什么、你缺乏什么。
书稿审读者和研究生顾问应将完美主义与专业水平区别看待。达到完美常常伴有专横霸道的行为。因此,控制狂最擅长教条谬论:他们不承认自己不完美,相反地,他们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别人的缺点上。他们无法抗拒让别人显得智力低下且道德败坏。然而,分歧可以得到表达,些微的争论可以进行,不必进行人身攻击。学者们可以因所作所为而出名,同时不显得那么恃才傲物。
我对学生说:善于指导的才是好老师。他们倾听着课堂的实时进展,关注各小部分是如何融为一体的。这需要一定的包容性,而寻求单边控制的人是不具备这种品质的。这要求教学大纲不妄谈学生的道德缺陷。要求教师不受降低标准的学术话语所诱惑,而学术标准往往错把顺从默许当作实际学习。学生不是玩物:他们是成年人,不应该必须成为教授才能通过课程。最重要的是,学者们需要明白:控制的欲望,一旦走向极端,都会显出固有的报复性,而这没有人需要。
我能理解控制的诱惑,尤其是当我们被夹在等级之间的时候。但是,当我们从破坏和微观控制中获取主动权时,我们只会持续助长高等教育的残酷火焰:学生无法抗议、持续容忍教师的哄骗;毕业生和求职者事事“完美”,却得不到任何回报;初级教师受阻于复杂秘密的晋升过程而与终身教职无缘;校园正日益成为一个监控学生、教职员工和行政人员的系统。当认为自己在维持严格秩序或维护标准,但是实际是滥用职权时,你很容易得出一种虚假的满足感。
这很诱人,我知道。而且它很快会失控。当那天第5个学生带来一篇混乱的论文找到我时,我很想告诉他该做什么——按照我的方式——而不是坐下来共同研究怎么办。我的学员对教育学有不同的方法:如果按照我的教学方式,那么她的那些课堂问题不就消失了吗?要是学生和我读书时一样勤奋就好了。要是他们穿得更专业就好了……
因此,我使用下面的策略来约束内心的控制欲。有时候,我会穿一件少了个扣子的衬衫。当我认错名册上的名字和人脸时,我向学生道歉同时取笑自己。我表扬学生,而不把它当作胡萝卜加大棒的招数。我改变每周在会议室的坐位,这样我很少在桌子的顶端。当一位同事坚持要第3次校对委员会会议记录时,我带他们出去吃午饭。当管理员被激怒时,我发给他们可以收养的动物照片。这些是我小小的反叛,它帮助提醒我,教育离不开不整洁、不完美但却美丽的人性。
道格拉斯·道兰系俄亥俄北方大学(Ohio Northern University)英语系副教授。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后记
Print headline: Let go of the whip hand